
一九四五年夏天,楊振寧在西南聯大附中完成一年教學工作后,踏上了赴美留學的征程。這并非一次輕松的旅程——當時中國與美國之間沒有正常的商船或航線來往,他不得不先乘飛機到印度加爾各答,在那里苦苦等待了三個月,才終于等到運兵船上的空位。
楊振寧和一組清華留美同學,一共二十幾個人,就這樣擠上了運兵船。每艘運兵船載幾千個在周邊地區的美國兵回國,船上留一二百個床位給非美國軍隊的人乘坐。船艙異常擁擠,人在床上甚至無法坐起來。船最底下的“統艙”里面有好幾百人,周圍都是美國兵。這是楊振寧第一次長時間接觸英語國家的人。
到了美國紐約上岸后,楊振寧花了兩天時間買了西服和大衣,隨后立即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尋找他心儀已久的物理學家費米。由于當時仍處于戰時,費米的行蹤一直被保密。楊振寧在中國時就聽說費米“失蹤”了,但他知道費米失蹤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所以到校詢問費米教授何時上課。令他非常驚訝和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書竟然沒有聽說過費米這個人。 后來在普林斯頓拜訪老師張文裕教授時,楊振寧才得知費米在戰爭期間曾在洛斯阿拉謨斯工作,并且已經決定到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這個信息促使楊振寧選擇成為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這個決定對他后來的科學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芝加哥大學,楊振寧與費米建立了密切的學術關系。費米除了教授普通課程外,還開設了一門特別課程,講授精選的專題。楊振寧深受費米的影響,同時他也與后來被稱為“氫彈之父”的泰勒教授有著深入的交流。泰勒的物理學研究具有鮮明的特點——他擁有許多來自直覺的見解,這些見解雖然不一定都正確(用楊振寧的話說,“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錯的”),但他不怕提出可能是錯誤的見解,這種勇于探索的精神給楊振寧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芝加哥大學的兩年半時間里,楊振寧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后來回憶說,這段時間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不僅是一般書本上的知識,尤其重要的是方法與方向。”他特別比較了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推演法和在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歸納法。在聯大,他通過吳大猷先生學習了分子光譜學與群論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從數學推演到物理的方法;而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注重的是從物理現象引導出數學表示的歸納法。楊振寧深刻體會到,因為歸納法的起點是物理現象,從這個方向出發,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楊振寧原本計劃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一篇實驗論文,他深感自己對實驗接觸太少。然而,由于當時他是外國人身份,不能進入阿貢國家實驗室,而費米的實驗室正好在那里,這個計劃未能實現。后來費米介紹他到艾里遜教授的實驗室工作,參與建造一套四十萬電子伏的加速器。在實驗室的十八至二十個月里,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實驗室有個笑話,說“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楊振寧”。
盡管付出了巨大努力,楊振寧的實驗工作并不太成功。他后來客觀地分析說,這倒不完全是他個人的錯誤,因為那個題目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做不出來的題目。當泰勒教授建議他改為撰寫理論論文時,楊振寧雖然感到失望,但經過兩天的思考后,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坦言,這個決定讓他如釋重負,后來他選擇了理論物理方向。對此,他幽默地引用朋友的話說:“這恐怕是實驗物理學的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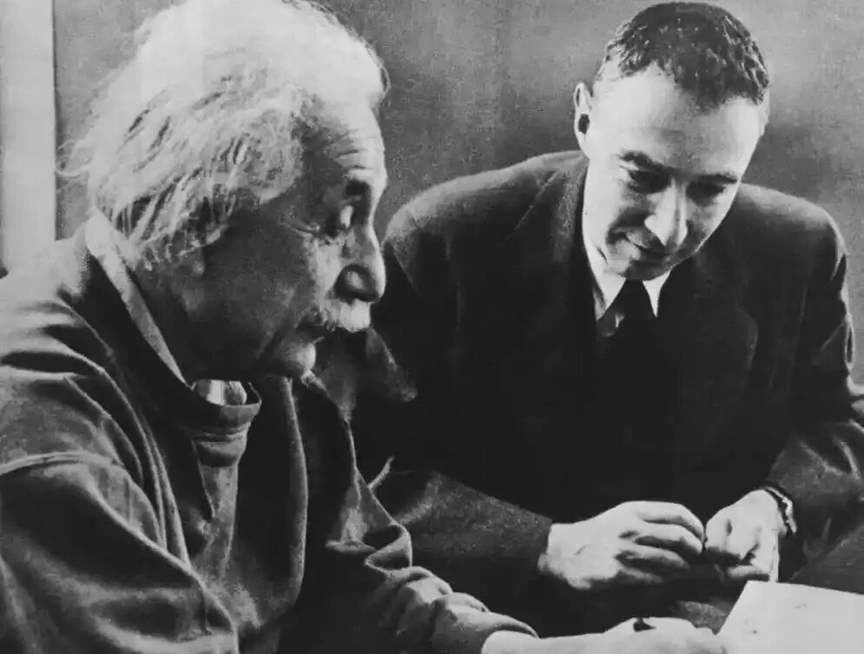
愛因斯坦(左)與奧本海默(右)
一九四八年獲得博士學位后,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做了一年的教員。一九四九年春天,當奧本海默到芝加哥大學演講時,楊振寧決定申請到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做研究。在泰勒和費米的推薦下,奧本海默很快接受了他的申請。費米在送別時給了他一個重要的建議:高等學術研究所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但不宜久居,因為那里的研究方向過于理論化,容易脫離實際物理問題,“有點像中古的修道院”。費米建議他去一年后就回到芝加哥來。
一九五〇年初,奧本海默聘請楊振寧長期留在普林斯頓研究所。奧本海默對楊振寧有著很高的評價,他曾經說過:“楊振寧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年輕人。”他還曾經開玩笑地說:“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我希望他能像楊振寧一樣。”
經過慎重考慮后,楊振寧決定留下。這個決定背后有一個浪漫的原因——那時他正在與杜致禮(后來的楊振寧夫人)交往,而她在紐約念書,離普林斯頓很近。

在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楊振寧迎來了科研事業的黃金時期。他特別回憶起與愛因斯坦的一次會面。有一天,愛因斯坦通過助手邀請楊振寧去談話,因為愛因斯坦看到了他和李政道合寫的一篇關于統計力學的文章。愛因斯坦年輕時的研究有兩大傳統:電磁學和統計力學,因此他一直對統計力學保持著濃厚興趣。楊振寧后來坦言,由于愛因斯坦的英文夾雜著德語詞匯,而自己又很緊張,所以談話后別人問起談話內容時,他竟說不清楚。

楊振寧(左一)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主要是一群年輕人經常討論和辯論,當然也有激烈的競爭。楊振寧特別強調,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是粒子物理學這一新領域蓬勃發展的時期,他和同時代的物理工作者很幸運地與這個新領域一同成長。他認為,一個年輕人在初出茅廬時,如果進入的領域將來有大發展,那么他能夠做出有意義工作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
在普林斯頓期間,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生活》雜志曾派攝影師來為楊振寧拍照,當時他辦公室桌子上堆滿了“預印本”。他本想搬掉再照,但攝影師堅持保留原樣。照片出來后,楊振寧幽默地說:“我才知道為什么他是攝影師而我不是。” 幾十年來的研究工作使楊振寧在統計力學和粒子物理學中的對稱原理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特別提到與他合作時間最長、最有成績的李政道和吳大峻,以及合作時間雖不很長但成果很有意義的米爾斯。這些合作關系的建立和發展,都與他在美國的學習和研究經歷密不可分。

今天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一九六五年初,楊振寧接到托爾教授的長途電話,邀請他到新成立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任教。經過幾個星期的考慮,他于一九六六年夏天離開待了十七年的普林斯頓,前往石溪。對于這個決定,很多人問他是否后悔走出“象牙塔”,他的回答始終是“不后悔”。他認為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業,比如建立石溪分校這樣的工作。
在石溪期間,楊振寧主持理論物理研究所,吸引了許多杰出學者前來訪問和研究,其中包括他做學生時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學家之一的狄拉克教授。他還特別提到一位來自韓國的教授李昭輝,認為他有深入的、直覺的物理見解,是杰出的人才。李昭輝(Benjamin Lee)在石溪的七年間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達到了一生學術工作的頂峰。
一九七一年夏天,中美關系開始出現解凍跡象,楊振寧立即決定訪問中國。他后來解釋為什么如此著急要去:“因為我看得出來,兩個國家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是在試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觸。當時越南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很怕這剛打開一道小縫的門在幾個月之內又會再關閉起來。”這是他二十六年來第一次回到祖國,內心的激動可想而知。
在中國的訪問期間,他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深刻感受到中國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他意識到自己可以成為中美兩國之間的橋梁:“回到美國以后我想我對于中國、美國都有一些認識,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這兩個大國初步接近的形勢下,我認識到我有一個做橋梁的責任。我應該幫助建立兩國之間的了解跟友誼。”1977—1980年,楊振寧出任全美華人協會(NACA)創始總會會長,為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友誼和合作作出重大貢獻。周培源曾評價說:“楊振寧是美籍華裔科學家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也是架設起中美之間科學家友誼和交流橋梁的第一人。僅是這方面的貢獻,楊振寧的成就就是無人能及的。”1981—1992年,楊振寧在石溪分校創辦的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CEEC)共資助國內81位(沈津和曾善慶曾先后2次受CEEC資助赴美)科學和人文學者赴美訪問進修,為中美兩國間的人才交流與合作作出突出貢獻。
回顧楊振寧在美留學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杰出科學家成長的全過程。從最初的語言文化適應,到學術方向的選擇,再到研究方法的形成,最后到國際學術橋梁的搭建,每一個階段都體現了他對科學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對祖國的深厚感情。他的經歷不僅是個人成功的典范,也是那個時代中國學子海外求學的縮影,更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頁。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些珍貴的經歷和思考,至今仍然對我們理解科學精神、國際交流和個人成長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文章中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和看法。
神州學人雜志及神州學人網原創文章轉載說明:如需轉載,務必注明出處,違者本網將依法追究。